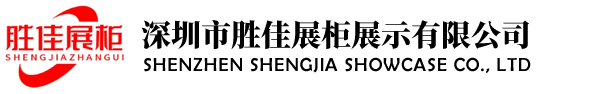
奧爾夫與一般音樂教學的比較1
要從精神本質上理解奧爾夫音樂教學的真髓,有必要將它與一般的、尤其是我國以往一般的中、小、幼的音樂教學作一比較。下面試從十二個方面來作對照和探討:(1)
奧爾夫音樂教學的精神
一般音樂教學的方式
從人的本性出發
僅從音樂教師的觀念出發
奧爾夫1931年寫道:“音樂始自人自身”。他這一論點和約兩千年前中國古代的《樂記》中的論述相符:“放歌之為言也,長言之也。說之故言之,窮之不足故長言之,長言之不足放嗟嘆之,嗟嘆之不足,故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也。”可是,經過幾千年的發展,中國的音樂教育,尤其是具體的教學方式方法,早已背離了這一基本思想。和封建教條緊密有聯系地,“師道尊嚴”已被發展向畸形和極端,從而從根本上忽視并抹煞的學生、尤其是兒童的個性、創造性和主動性。教師往往不善于、甚至不懂得學生應是學習的主體,而不僅是教師進行教學的客體。奧爾夫、柯達依等許多音樂教育家都曾指出:人生而具有對音樂的喜愛和感受能力,尤其是兒童;完全沒有樂感的兒童幾乎不存在。不認識、堅信,并牢牢記住、抓住這一點,并作為音樂教育和教學的出發點,往往只能事倍功半,甚至貽誤學生。
音樂教師應當逐步意識到:奧爾夫音樂教育體系最本質、最重要、也最有意義的東西,首先在于它不是一種方法,而是音樂教育基本理念的集中體現:從人的本性出發,經過自然性和整體性,達到音樂性的完滿。任何一位音樂教育工作者,尤其是在課堂第一線執教的教師肩負有重大、神圣而又危險的職責:或是使孩子心中的音樂火花燃起,或是使之逐漸熄滅;換句話說:或是幫助“小莫扎特”在音樂上成長,或是使他的樂感(甚至對音樂的熱愛)窒息手搖籃之中。這決非危言聳聽的夸張,而是常見的事實。
音樂教育和教學如果僅僅停留和局限于教師個人的觀念和意愿,而不是從學生的本性和能動性出發,是難以收效的。(2)
杜絕強制,使個性有充分發展的可能
強制起支配作用;有或無意識的抹殺個性
音樂的生命離不開自然和人性,倘若自然和人性被扭曲或扼殺,音樂也必然被窒息。中國有幾千年封建主義的歷史,從而必然會在各個方面投下它的陰影,包括在審美方面或音樂教育和教學方面:古今多少文人、畫師、學者和富貴人家的風雅人士,盆栽梅花慣于用繩索捆扎,使梅技扭曲,以呈現出奇姿異態,以致龔定庵(1792—1841)撰寫下《病梅館記》加以痛斥。作為音樂教育工作者,難道不應當從中得取教,也像龔定庵那樣對一切非自然和反自然的現象和審美,作出堅決的抗議嗎?!當我們觀看中國許多孩子們在歌舞表演中的許多動作,難道不能看出那些動作和表演,從設計到具體細節,不都是出自教師們(包括編舞者),而不是出自孩子們自己嗎?難道不能看出有無數根看不見的繩索,在木偶一般的孩子們上方和后面牽動著嗎?孩子們進行非個性化的表演和動作,正是本末倒置不可避免的結果。如果看到這種情況,不感到有問題,反而會認為這些孩子們“乖”、“聽話”、“學得好”、“做得好”,那也正如同不以病梅為病,反以為美的審美』動態一樣。強制難以產生出健康和美,更往往是自然和純真的大政。正如諺語有云:“常受扭曲的植物,斷難繁茂生長”,如果把教育和強制混為一談、成為一體,只能培養出精神的奴仆。(3)
強調樂趣,并通過啟發,不斷促使學生思考,磚研,能動地嘗試和實踐
只過分的強調“勤學苦練”;教學基于并局限于教師的傳授和教導
中文的“樂”字有兩層涵義:音樂與快樂,盡管包問一個字有兩種不同的念音。按字義淵源學考據:這個吉寧手剪足“材,上方兩側的“么”系指絲(弦),即:意為在一坑木上張著弦,從而在這樂器上奏出音樂,使人說樂。這雄辯的說明:在中國古人心目中,音樂是和歡樂并列在一起的。但是,隨著時間的推移,在正統的孔教和否定人性的封建禁欲主義支配下,(音)樂的這一層附帶的含義日益淡薄。《樂記》中并不否定“夫樂者樂也,人情之所不能免也”(《樂代目》).可是,封建的禮樂觀決定了引向極端的歷史發展:片面強調和利用音樂的教育功能,而竭力節制音樂的娛樂功能,盡管大多數的帝王、公候和富貴人士,事實上自己耽溺于聲色享樂之中難以已拔。不少人往往只知道或只強調“寓教于樂”,而認識不到在這同時也有“寓樂于教”的必要性。只知道刺股和囊螢積雪,并以此去教導和要求學生,而不懂得去誘發學生對音樂學習本身的興趣和樂趣,那就難以成為一名真正的奧爾夫音樂教師。古今中外,不論專業或民間的音樂教育,往往只知道或習慣于全面地口傳心授、一味模仿式的教學,而缺乏循循善誘的啟發,并調動學生學習的能動性、自發性和創造性。這種通病并非短期內即能治愈的。尤其是音樂教學,不是單憑“勤學苦練”,或只通過知識傳授和技能操練,即可被掌握的。要在音樂藝術王國中登堂入室,絕不可能單憑“苦練”這條通道。勤奮和練習,是必備的素質和前提,但不一定是學成的保證。勤奮是中國人(包括孩子們)優秀的品質和傳統的習性,這種精神和學習態度應當繼承并發揚,但是,不講求樂趣和效率,只知道盲目或一味地勤學苦練,則只能說明教育的無能。我們不應要求并把尤其是孩子,培養成苦行僧般的“好學生”。
只知道勤奮和聽話,而不懂得尋求并體會樂在其中的音樂學生,不會是真正的好學生,也不可能成長為真正的音樂主人。(4)
訴諸感情,強調直觀性
訴諸理性,以口頭傳授為主
中國藝術自古強調意境和傳神。按中國傳統的藝術審美:音樂作為一門藝術,不止于表現思想情感,更在于精神和意境的體現,所以歷來有“只可意會不可言傳”的說法,而對于意境,首要的在于“心領神會”。可是,在我國一般的音樂教學中,往往忽視了對心領神會的啟迪,從而背離了訴諸感性、強調直觀性的原則,而使得音樂課似乎和上化學、數學課,沒有多大的差別。教師疲于喋喋不休地通過說話來教,學生則忙于
通過聽講和記筆記來學,然后,除了死記硬背和操作技術以外,似乎沒有別的、更好的辦法。
兒童音樂教育和中、小、幼的學校音樂教育,教學對象是孩子,因此更需要通過訴諸感性的、具有形象性和直觀性的教學方式進行;所教的是音樂,這是一門首先訴諸感性的藝術。教兒童和教學專業音樂學生和成人一樣,只有程度深淺和難易的區別,而沒有本質的差異。音樂的軀體是聲音,不是有固定概念性含義的聲音,所以,對于音樂語言,應當有別于一般語言文字的學習、理解和教學。只有通過訴諸于感性,使學生能心領神會,才能領悟和掌握音樂自身的語言、規律和美。(5)
主要通過唱奏音樂實踐去學習音樂
主要通過教師的教導去學習音樂
奧爾夫音樂教育,要求學生通過心、頭、口、手、腳,以至全身去投入實際的唱一奏一跳一演,來學習和掌握音樂。音樂教育和教學最好的途徑和最重要的原則,就是自己去進行音樂實踐,而這在中國一般的音樂教學中,卻往往被忽視。往往只偏勞了口:教師說話說得累,學生們一味作單調的模唱和齊唱唱得累。
近年來國內學琴熱如火如茶,這不也是音樂實踐嗎?當然是。可是應當看到:那樣的音樂學習,很大一部分并不出自于、也不著眼于學生們對音樂的喜愛,而許多家長不問那音樂教學的音樂質量,并不理會是否在打下音樂教化的基礎,而常常抱著學了琴、考了級,能“加分”、能炫耀的心態,或甚至日后學成,能成為“神童”、“莫扎特第二”或“國際比賽得獎者”的最高希望,去鼓勵、鞭策自己的孩子勤學苦練。不講究兒童心理學和器樂、聲樂教學的音樂教育,在文化上和藝術上是不可能收效的。在鋼琴、提琴這一類演奏技術十分艱難的樂器上,脫離了音樂的藝術要求和心理的愉悅,只去苦練和死后技術,學習者對音樂的興趣和創造性,會被貽誤或磨損。充其量只能造就也樂匠,而不是音樂之友或音樂的知音,更遑論音樂的主人。(6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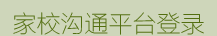
- 幼教資訊 >>更多
- 幼教展會 >>更多



